“理论热”——从现象开始
| 2012年05月0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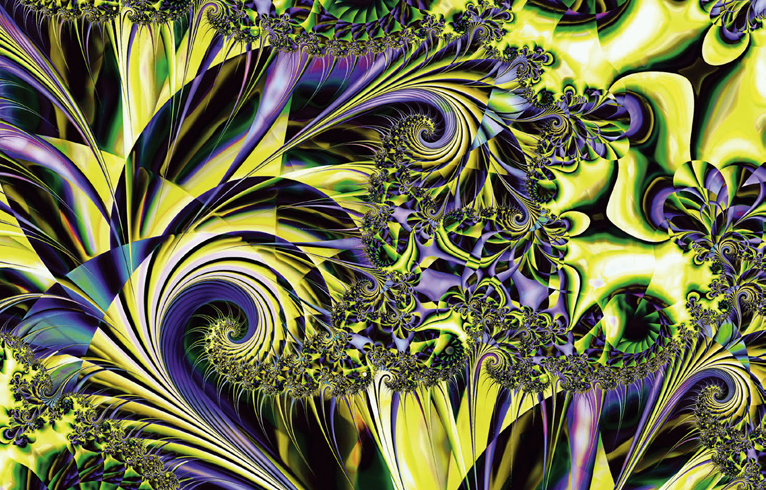
从85新潮开始,理论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并经由几次“论战”掀起高潮。1980年代初突如其来的开放空气使得西方理论涌入,从质量参差不齐的译本中萨特、存在主义,到后来大量翻译进中国的后现代理论;1980年代有对“抽象美”的集中讨论,到1990年代中期又有邱志杰以《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和随后的“后感性”实践冲击易英等代表的学院权威;而进入2000年后,市场繁荣,“批评文章沦为画册装潢”。时至今日,旧话重提,以2011年微博争论为最初的提示,我们发现,从理论工作者到艺术家,甚至到学术和艺术爱好者,很多人都有发言的冲动。
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现阶段我们所谈论的理论的热与不热都是在中国艺术圈内展开,它虽然也处在全球背景之下,但仍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而被讨论—中国并不自产我们现在所泛指的哲学和艺术理论,更没有再反向销往西方的理论,不过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诸多问题,使得它成为一个极为丰富的研究客体。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此有着相异的总结,无论是从艺术家创作出发的“艺术家自身的理论冲动”,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照着理论做艺术是早期中国艺术家的一个生存策略”,“理论之于中国当代艺术”这条既不严密又充满起伏的关系线其实一直存在,它曾经为学院权威的强势而受到压抑和进行反抗,也曾经因为市场的热闹而淹没了声息,不过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引进、阅读和运用仍然是一个长期和常态的过程。在我们接触到的大量人群中,不乏专心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翻译引进工作的“书斋型学者”,他们埋下了一条潜在线索,虽远离现场但提供参照;学院内部混合了理论和创作的“理论状态”的实验在摸索中进行;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自身对于知识和理论的吸收也以个体行为的方式继续。而眼下已经摆在台面之上的“热”的现象更无法回避,它和网络平台的出现有关,和个别关键人物的刺激有关,也和中国当代艺术30年发展的节点有关,话题本身已经在显露形状。

一种理论需要
活跃于艺术圈中的人对于公共平台如微博和论坛上的讨论,以及嬉笑议论如开幕饭局和私人聚会上时常出现的话题都不会感到陌生,没人没听说过ABRZ(阿甘本、巴丢、朗西埃和齐泽克)。众多微博ID背后隐藏着的是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性格:严肃的、围观者,有人炫耀知识,有人在摆立场同时要求别人给出立场,有人冷眼窥视他人言论,不一而足。而既然有所谓“时髦”,相应就有人反其道而行,但“不谈”的未必没在暗暗用力;而ABRZ之外,也有人更乐意向维特根斯坦甚至于柏拉图中去找寻自己所需。
2011年“理论车间后门”(陆兴华)在微博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无论他和他的反对者、反感者如何互相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谩骂,争论如何从学理、社会事件快速转向对个人价值观和人格的谴责,在大量无效的素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倾向,理论的问题再次进入艺术圈视野,哪怕只是“谈及”而非“谈论”,只是这一次,网络,尤其是微博承担起了舞台的作用。而这个平台本身的一些属性,碎片化、即时性,都让“热”的真实和扎实程度蒙上了一层阴影—网络无法提供一个深入的谈话环境,它的开放也不能等同于参与者心态上的开放,相反,对立在这里是如此容易形成,以至于在争论的结尾处人人都怅然若失,回到一个最幼稚的问题,为自己的情绪收拾残局。
如果对比1990年代中期的一次“理论热”,邱志杰回忆当时他和易英在《江苏画刊》上的笔战,有前期研讨会上的立场分化为序曲,“经过了深思熟虑,集中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如此粗略地概括这些事件并非要简化和削弱它们在当时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只是在一个知识占有和发言权力都完全平面化了的时代,从前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也无法留恋。当阵地已经从《江苏画刊》这样的杂志转移至美术同盟这样的论坛,及至再往后出现的art-ba-ba和微博,与体制、权威的贴身肉搏变成了一种已经“合法化”了的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的自反活动,新的、有效的模式究竟是什么?
抛去网络上可能存在的表演成分和刻意挑衅,陆兴华作为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参与艺术圈更早于微博:2010年的胡志明小道他是同行人员之一,他和高士明的关系又更要追溯到高的学生时代。高士明随后在2010年上海双年展策划了“巡回排演”,一众艺术家参与其中。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去看,中国美院跨媒体系的整个教育方法的实验,邱志杰的“总体艺术工作室”,甚至杨福东“片场”式的课程安排都可以视作处在框架之内。而2011年初金锋等人邀请陆兴华在桃浦组织讨论会,没顶公司的加入和幕后推进,“未来的节日”渐渐成型并有了自己的首次展览。以理论/理论家来刺激创作的方式在此处被更明确地提出,又因其态度的极端而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和攻击的典型案例。
外界的猜测纷纭,此举是否功利,功利的成分有多大?究竟谁在利用谁?背后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学术脉络?甚至陆兴华本人的学问究竟是否靠得住?就金锋的话来说,他们作为艺术家更需要的是被质问,在陆兴华一遍遍的“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提问下做出反应。回到工作室后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疲软”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圈对自身的切实体会,艺术家们需要在粘滞状态中找到出路。“理论指导实践”这个哪怕在短短30年内都称不上新鲜的方式再次出现必然引来质疑—这同中国当代艺术早期需要借用西方话语来找到自己的观众群和市场是否存在差异?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本身的参与度究竟有多大,似乎倒成为了现阶段的一个次要问题。但就像邱志杰在提到陆兴华时所说,无论他观点对错,对理论的解读深刻与否,中国艺术界都应该对此人感恩戴德。“感恩戴德”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攻击和刺激的方式的确把问题推到了台前并且穷追不舍地一再刺痛。对于哲学家来说,艺术成为其素材和研究对象,而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找刺激”显然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答案。
作为一个身份复杂并且熟知本土艺术圈现状的人士,皮力的说法给出了另一个角度。“为什么现在要有一个理论热和理论需要,这是个历史化的问题,三十年艺术发展积累的素材足够丰富,我们要开始历史化的梳理了。这个问题今天变得很迫切,是因为我们本土文化到了开始需要自我评判和自我阐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权力,又不想把这个权力交给国外,也不想交给市场。”他建议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不是由形而上进入实践,而是从艺术家个案分析、艺术现象的分析做起,使用何种术语和何种理论方法则在此过程中产生。从批评家到艺术媒体都需要分担一部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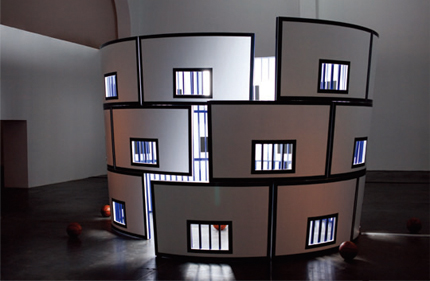
一种理论状态
“在你做艺术之前,你就得明白艺术是什么。如果你从事的是某种已经确立的艺术形式,比如书法,那么你可能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但艺术在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你必须在做事情之前对从事艺术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确立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你在面对社会、市场和艺术机构等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艺术家无需考虑理论和哲学问题的建议在几百年前适用,但在我们的时代,传统已经逝去,这已经不是一个好主意。无论美国、欧洲、中国、印度,整个世界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牵扯到各种理论,你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理论上的位置。”我们在北京见到鲍里斯·格罗伊斯时也不可避免并且不失时机地问到了这个问题。格罗伊斯的回答亦不新奇,但也明确地点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艺术家”这个身份已经不再具备经典意义上的那种封闭性,每个人都被搅进了同一个战局。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的身份必然地交织重叠又产生对抗。
“我所理解的理论应该是一种更加活态的东西。”高士明说,“一种创作性的理论,一种‘理论状态’。不要被类型的分野迷惑,比如我们讨论艺术和政治,讨论都是‘那个’理和‘那个’经验,无非说我们很难用既有的词汇去称呼它。如果真的分成艺术和政治两个领域的争论就是庸人自扰。理论家在这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最起码的应该是体制批判,这里体制指的不是美术馆体制或者双年展体制,这个体制是无形的。”他用艺术家状态和理论家状态来概括他们的“冲动”,“不是艺术家管创作理论家管总结和理论化”。“当代艺术不完全是视觉的,也是观念的、关系性的、体制的、反体制的、政治的等等,它是无数个词所共同描述的实践,非常复杂。”他的说法也反映了国美这些身兼教职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的一种基本共识。回到创作,高士明以吴山专为例,“分不清它是理论状态还是创作状态”。其他如我们平日观察,粗略划入“理论型导向”的艺术家名单中当然还有如邱志杰、汪建伟等,去接触这一类作品时往往会让观众感到困惑及不信任。
说理也易陷入诡辩,理论和创作的互相介入也有“不落地”之虞。“从前有过提反对点子创作,但后来这个变成了故弄玄虚,完全没有解释和阐释,给观众带来的也不是智性的价值,只是景观。”青年批评家鲍栋说。“‘对智性的尊重’未必要通过理论,但理论是比较有效的。当代艺术圈要比别的圈子好多了,但还是有种对‘智性’的不信任和无知,对知识、思维的反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陆兴华一次次“终结”式的断言也不妨碍像杨福东这样虽然参与过桃浦的集体讨论但“自己私下也在搞艺术”的艺术家(在陆的框架内,单个作品无关艺术),在陆“展示大于创作”的说法之下,杨福东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显然是失效的。而邱志杰亦会把杨福东的工作方法定义为“思”而非理论,但仍承认其有效性。艺术家身上是否同时也要承担策展人和批评家的角色?所读理论是否定要和自身创作相关?是否人人都需要一种理论状态,尺度如何把握?“说”是否是种必须?回到格罗伊斯所说“理论上的位置”,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意识而不是附加条件,创作类型的多样和复杂也是艺术的吸引人之处。当然无论陆兴华还是邱志杰的提法也不过是众多维度中的一支,甚至都不是最主流的一支,背后更是有着各自的出处。虽然小范围来看,在一种不激进即反动的恐慌下,被洗脑和被激怒的危险同时存在,但完全屏蔽也属消极选择。中国当代艺术即使作为一个“先天不良”的产物,要为自己眼下的状况进行反思和推进,无论是这个时间点上的一种理论需要,还是需要长期经营的一种理论状态或者理论生活。

“热”
借用高士明在谈及他担任策展人的2010年上海双年展时所说,虽然同处一个展览,胡志明小道的艺术家和张洹、刘小东并未发生任何关系。“大家都是自己竖了个墙彼此隔膜起来,中国当代艺术里不同系统间是没有打通的,既没有对话也没有斗争,加上艺术资本的作用,就变得更加混乱不堪。”这个评判当然并不专指理论问题,但在关于理论的思考中同样适用。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在“语境”之中的艺术圈时,可以充分感受到“理论热”的热度,甚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范围扩大,热度也随之稀释。对于那些“已经建立”的艺术家来说,对话的状态显然是不对等的;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还无暇被真正顾及,几次“外围式”的座谈会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自发式的学习和交流也难免缺乏重点。即使在我们关注的内部,对话的障碍也无处不在,成见、利益,甚至人情,围墙的形态各异,并且很多历经30年依然健在,从对于各自的理论源头和实践方法的“揭露”和“指责”中可见一斑—后殖民理论是否为了迎合官方中的“清流”,身肩生意的人又是否已经自动放弃了学术研究的资格?“在同行和共事中,人们慢慢对对方变得敏感,达到默契,当然这个默契也不是指互相同意”,邱志杰描述的自然是一种理想和美好的状态。
最后回到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市场的巨大作用往往让在前期的反叛、激进变成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并且不仅仅是在中国,这是一个时代对处于它背景之下的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几位当红理论家的流行也和此不乏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打破僵局。而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无论是因为南北地域的间隔,还是借用了法派和英美研究方法的分歧,甚至是不同群体间性格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偏见和隔阂,则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中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内忧外患”。但“理论热”的出现,艺术圈的卷入,不知是否可以在“行动”中制造出一种可能—开始清理偏见,让“理论热”产生根基并开始生长,由病理上的“热”变为常态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