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s
| 2015年03月24日
香港刺点画廊
2014.11.15~2015.01.10

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广当代摄影的机构,刺点画廊在肩负使命感的同时也透露着某种危机感,正如其宗旨中写到的,当代摄影仿如进入“盲点”,已成为一种“被忽略”的艺术媒介,这样的危机感亦隐约渗透于他们最近的展览“780s”中。如字面所显示的,此展展出七位生于1980年代的香港艺术家的摄影及混合媒介作品,意在呈现当下“图像泛滥的数码年代”里,他们如何思考及使用摄影这一创作媒介。
本雅明1931年的《摄影小史》尤在慨叹“摄影要向绘画接过传承的火炬”,时移世易,如今摄影自身又在经历媒介更新带来的挑战。与其说这七位艺术家选择摄影作为创作媒介象征着某种坚守,倒不如将其看作是对于摄影相关议题的持续探讨。如果摄影得以超越绘画的论据在于它对事物真实性的无限接近(罗兰·巴特将此视为摄影的实质),那么这个论据也早已被动摇,今日摄影之实质毋宁说是“似是而非的真实”。正如曾家伟的《花布》,唯有走近它才会发觉,这些如同纺织厂批量生产的色彩纷呈的“花布”实际上是由有序摆放在黑色土壤表面的繁花所构成,在镜头下它们被取消了立体感,满幅的构图,以及摆放在一侧的碎花帆布鞋则加强了这种刻意营造的平面化效果。同样的视觉骗局出现在赖朗骞的《靠墙站》系列中,他用一部普通手机拍摄了大量低像素照片,细节的丧失导致感知的钝化,从而使观者无法察觉到照片中那些人物的面部特写,只不过是艺术家对一张海报的近距离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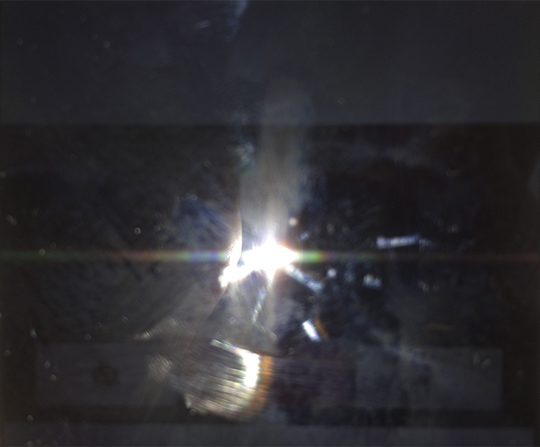
赖朗骞的低像素影像之另一重隐喻在于,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拍摄者与摄影艺术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当拍摄行为与社交网络结盟,私生活则又与公共生活难分彼此。张伟乐的创作颇主动地介入这类议题,他将自己在脸书上被朋友“Tag”的照片投放于银盐相纸,利用传统的洗晒方式完成了黑白负片效果的“自拍”。陈泳因和杨沛铿的摄影毫无掩饰地展示其私密特征:前者的《27. 0》由自己的身体局部、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物件和角落组成,似乎在邀请公众窥视她的私人生活;后者的《酣睡床》系列则持续拍摄世界各地的旅馆中那些与他同处一室的、正在酣睡的陌生人,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们建立起联系,而相框玻璃上,沿着人物身体起伏所雕刻的抽象图案仿佛代替艺术家抚摸着陌生的室友、抚摸着抽象的情感联系,不经意间增添了些许浪漫色彩。
对于萧伟恒与何兆南而言,作为媒介的摄影可以自如地与其他媒介相结合而无需担忧自身有效性的缺失,在此展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边界”作为主题。萧伟恒的《境内景外》包括了摄影和录像,从香港边境拍摄对岸的中国大陆,借此传承父辈的生存记忆。《防卫与抵抗》记录了何兆南的一次行为:他用印着“香港制造made in Xianggang”的砖头垒起松散的防线,并将自己围在内,这固然象征着香港社会现状,却巧合一般地指向了此展的立意—一种预设传统摄影已式微、试图重新构筑其边界的焦灼状态。但就像本雅明早已指出的,对于摄影的讨论总是局限在“摄影作为艺术”这一层面,却甚少关注“艺术作为摄影”这种更具有社会内涵的议题。沿着本雅明的思路,如果跳出艺术的框架,从文化史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摄影,才有可能得到更宽广的答案,至少,也可以稍稍抚平画地为牢带来的不必要的危机感。
武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