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中的史莱姆
| 2023年11月08日
“怪物是我们的孩子,它们可能被赶到地理和话语的最远边缘,被放逐到我们的世界和心灵深处的隐秘处,但不可避免地,它们会回来”。[1]
——杰瑞米·杰弗瑞·科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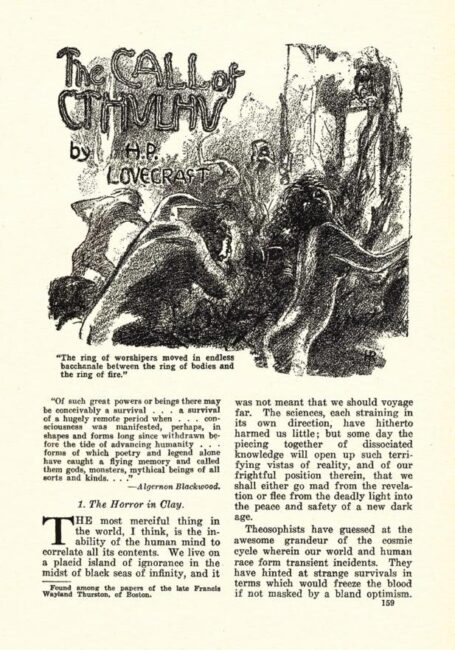
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的呼唤》在《怪志》中的标题页,1928年2月
网络开源图片
近年来,“湿滑物质”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诸多艺术作品中,其符号意义也在当代文化的论述空间内不断被提及。关于它,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恐怖科幻文学与电影创作不能被忽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深藏在未知之域的克苏鲁。克苏鲁首次出现于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1928年发表于杂志《怪志》(Weird Tales)中的短篇小说《克苏鲁的呼唤》[2],但如果向前追溯,哥特文学中的腐烂景观也能发现它的踪影。在《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玛丽·雪莱,1818)中,怪物诞生时的湿润眼睛被一片肮脏混杂的阴影所笼罩,它永远摆在存在的边缘——科学意外产生的黑箱,在那一片湿润模糊的屏障背后,是人们对彼时技术跃进和加速的不安。[3]此类粘稠物质好像自此总是与怪物关联起来,二十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一次核能测试的爆发与人类对地外文明逐渐高涨的好奇,它们愈加频繁地出现在电影与小说中:1958年上映的电影《史波吉》(The Blob)中,一个由史莱姆菌组成的高大实体出现,它吞噬所到之处的一切,对人类社会构成了直观的威胁;约翰·霍金(John Halkin)发表于1984年的小说《史莱姆》(Slime)则刻画了一群居于海底深处、极度渴望蚕食人类的胶质生物;延续近四十年的《异形》(Alien)系列通过粘液意象成功地唤起观众对主角Xenomorph陌生又原始的恐惧。
无形的湿滑物质是一个强大的符号。它流淌而润滑,留下变形的痕迹和怪异的感觉。肉身放弃了其本质,陷入一种湿滑的分解状态,超越了所有形态界限。这个过程也在折射观者从结构性的秩序世界滑向毫无头绪的混沌迷宫时所伴随的深刻忧虑。就像事物总在趋向混乱的过程,被推向边缘与禁区的怪物般的史莱姆也总会回归。人类作为主体对世界的把握被打断,诱发压抑和恐惧的对象复苏。它们在人类的文化想象中不断浮现,以不同的方式循环并与我们连接。
循环 I
展台上,一滩粉色泥状物脉动着,发出低沉咆哮般的噪音。它是马兹·贝林·克里斯蒂安森(Mads Bering Christiansen)与乔纳斯·约根森(Jonas Jørgensen)创作的名为《SONŌ》的软体机器人,为了让它更具生气,艺术家汇集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流行电影中出现的怪物声音。《SONŌ》的身体由一种常被运用于好莱坞特效的硅胶构成,这使之具有生物肉体般的柔软。它的形态呼应着银幕上不断出现的史莱姆状物。艺术家试图通过这个离奇的“生物”及其音景来质询生命,或者说活性(activism)的本质,展示出主体与客体间循环往复的互渗。《SONŌ》与前文中提及的那些怪物一样熟悉又神秘——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广为人知的著作《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中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并阐释了“卑贱”(the abject)这一概念——我们得到一种被从象征秩序的领域驱逐出去、引起个体内部恐惧和排斥的异化实体。[4]《SONŌ》中,艺术家创造出卑贱物去试图质询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它”存在于自我之外,却又与之紧密相连,永远徘徊在过渡的领域中。被看作生物分解残留的史莱姆状物是一种奇特的废弃产物,它跨越了存在与消亡之间的脆弱界线,连接着有机与无机、有生命与无生命实体。
尽管我们经常从一个安全的距离、透过平滑的界面看这些肮脏实体,将它们看作卑贱物,我们却也应意识到,怪物与我们的联系不仅仅停留于表征层面,它们也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与我们共存。

詹娜·苏特拉,《nimiia cétiï》,2018年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Somewhere House,伦敦
艺术家詹娜·苏特拉(Jenna Sutela)在其影像作品《nimiia cétiï》(2018)中关注到一种细菌——枯草杆菌(Bacillus subtilis)。这种细菌会形成一层粘液状的薄膜,覆盖在城市里阴暗潮湿的角落的水管上、我们的胃肠道中,也处在前往火星的过程中。苏特拉运用机器学习解读源自枯草杆菌运动的信息,并基于十九世纪末法国通灵者埃莲·史密斯(Hélène Smith)所传达的火星语(埃莲·史密斯声称自己在一次陷入恍惚状态时被带到火星,并在那里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生成了一种新的书面和口头语言。苏特拉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人类,因为我们的身体中寄生着大量的细菌,外星人就在我们体内,并通过肠脑连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情绪。[5]
黏液和凝胶状物质在人类肠道微生物组中的确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作为保护屏障存在于宿主和肠道微生物居民之间,防止有害细菌渗入宿主组织。与此同时,黏液层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这些细菌有助于消化和其他生理过程[6]。黏液层及其所支持的微生物群落是人类作为共生体(holobiont)——将人类视为既包含人类细胞又包含微生物细胞的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
也许正是因为史莱姆在我们身体中的存在,才使得它具有一种深植于我们内部的原始魅力,时刻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与想象。19世纪60年代,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提出了“原生质”理论,并将其与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的概念相结合。后者认为细胞中存在的复杂胶状物质包含了生命所需的基本元素。赫胥黎将原生质视为生命的物质基础,能够执行新陈代谢、生长和繁殖等各种功能。赫胥黎的理论揭示了令人着迷的景象,即细胞中胶状和半透明物质不溶于水,并可以表现出类似粘液的特性,具有可伸展的能力。由此,最微小的原生质单位也可以成为生命的基本构建块,类似细菌和变形虫;它们具有像拼图一样奇妙的融合能力,能够产生复杂的有机体。
赫胥黎的理论最终未经受住科学验证的检视,被搁置在历史中。然而,科学家们对原生质的想象并未仅仅停留在将其看作一种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它更是一种动态介质,伴随着能量波动和生物物质的流动而脉动。这种胶状物质敏感、可收缩,并以波动的形式运动,这促使科学家们将原生质与传输波动的其他介质(如以太)进行类比。类似波动传播的原生质行为表明,它可以作为生物体内能量波动和生物物质运动的介质。正如哲学学者本杰明·伍瓦德(Benjamin Woodward)所指出的那样,原生质更像是一种认知物(epistemic object),一个连接了物理与生物过程的试验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物质主义与机械主义相连接。这为打破物质主义和机械论之间简单的二分化奠定了基础,并丰富和重塑了围绕美学的讨论。[7]
循环II
生物膜或微生物集群这样的史莱姆物质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每个栖息地中找到。这些黏滑的社群对营养循环、废物分解和疾病预防等生态过程至关重要。海洋生物学家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提出了“史莱姆时代”的可能性 ,或可称之为“史莱姆世”(Myxocene)——这是一个海洋被黏液占据的时代,海水中充满了无数浮游生物。正如《史莱姆:一段自然史》的作者苏珊娜·韦德利奇(Susanne Wedlich)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8]。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些社群能够繁殖的条件,从而使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发生转变。史莱姆世仅仅是人类世、克苏鲁世、种植世等名称的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史莱姆无状之形的本质和卓越的适应能力使其既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强大力量,又成为了一种潜在的不祥之兆,其滋养的开端即是吞噬的终点。古生物学家彼得·沃德在他的著作《梅狄娅假说:地球生命最终会自我毁灭吗?》中,将这莫比乌斯般的过程与古希腊女巫梅狄娅进行了比较。梅狄娅在被背叛和抛弃后,为了报复而夺走了自己孩子的生命 ——“杀手即是生命自己”[9]。

马兹·贝林·克里斯蒂安森与乔纳斯·约根森,《SONŌ》,2020–22年
摄影:朱磊
图片致谢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的感知。它通常在危机情况下变得异常敏锐。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认为,只有被视为正常的事物后撤,哥特式的暗黑生态显露,现实的一角才得以被人类鲜活地感知到[10]。史莱姆作为一种介于有形与无形间的物质在此变为了一种联通我们感知生态的介质。关注黏液的研究者与电影制作人弗莱迪·梅森(Freddie Mason)曾说,“粘稠并不存在”,即使它们无处不在。这并不只是说粘稠是形容词,不指代某一特定的事物,因为他随即将史莱姆解释为粘稠具有轮廓后的形态——但是粘稠与史莱姆都处于一种幻想状态中,他们是“事物无法被把握的状态,热切地溶解于思想活动,是一种存在与感觉通道”[11]。
在这一通道中,卑贱性从人类建构的自然概念中被释放,主体观念下的崇高被粉碎。我们最终意识到梅狄娅的故事中以及与史莱姆的缠绕中存在着的循环。然而,莫顿认为还有另一个循环,它的起点远早于工业革命这一被视为人类世的关键时刻。

史莱姆菌种多头绒泡菌
网络开源图片
循环III
当更新世的冰川在约12500年前开始融化,气候逐渐转暖,人类捕猎与群居的生存方式开始转变为农耕与开垦。在这个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文明摇篮之一。它发源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之间,由于常年高温与低降雨量导致土地干涸。当地居民为维持稳定的收成,掌握了灌溉与土地规划的技术;同时,其南部区域内高低错落的地势所造成的泥沙堆积经常诱发两条河泛滥,使得土壤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物。在两者的结合下,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其南部,能稳定地培育高产量作物,此处的居民也开启了定居生产模式。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图
网络开源图片
莫顿将此视为“农业后勤学”(agrilogistics)的诞生,认为人类便是在这一时期将农业塑造成“自然”,以便将生态转化为资源池。人类看待生态的方式也即转变为如何运用技术高效率地规划、利用这些资源。由此看来,工业生产中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也是“农业后勤学”在工业革命后时代中的延伸。与其说“我们从未现代过”,莫顿坚信我们一直都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即使是在环保主义盛行的今天,莫顿认为我们依然在以“农业后勤学”的方式理解生态,也正因此,我们从未逃离过与生态对立的循环。[12]
源于自然、投射了人类想象的史莱姆似乎也可被放置在”农业后勤学”的框架中。单细胞黏菌所拥有的强大去中心化集体智能总是吸引着科学家,它们对应复杂空间问题、集体决策与资源配置的出色表现在生物学、人工智能算法、城市规划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尤其是黏菌间相互连接的细胞网络通过化学信号进行沟通和信息交换的运动模式[13],被视为一类强大的模型。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就在其著作《诸众》中将集群智能的概念挪用至描述一种如怪物一般(monstrous)无序的诸众力量。他们强调这种力量的本质是一种“民主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构成并不仅仅是指灵活的、去中心化形式的结构,还涉及如何共同产出社会性的内容[14]。而只有通过沟通,分布在网络中的代理才能生成新的信息或知识,从而构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让他们在行动中仍能保持多元化。

马兹·贝林·克里斯蒂安森与乔纳斯·约根森,《SONŌ》,2020–22年
摄影:朱磊
图片致谢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不论是在今天主流的科学媒体,还是在哈特与内格里对“诸众”的研究中,他们都试图通过后人类姿态去对各自领域中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非人类智能因此得到关注,并被畅想着基于它们的未来。但是,如史莱姆菌这样的非人类实体依然未跳脱出它们符号化的象征性,尤其是在哈特与内格里的论述中。这种简化仍将非人类实体的“怪物性”困在一个以人类中心、物种主义的框架中,并无意中延续了一种殖民主义的观点,强化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支配性等级观念。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小说《索拉里斯星》(Solaris)描绘了一颗被广阔的胶质海洋所包裹的星球。地球科学家们推测,这片海洋是一个独立而有智慧的实体,便试图对其进行研究并与之建立沟通。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宁静的海洋对这些接近保持冷漠,也使得它避免了被物化、被人格化后所可能导致的悲剧。不仅如此,它还制造幻象迷惑地球人,让他们直面自身的欲望和恐惧,却未暴露任何关于其自己的信息,只是呈现出一种“看似理性……但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活动”。在史莱姆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的、即将超出我们控制的卑贱和怪诞。就像地球人和《索拉里斯星》中那片海洋的结局一样,在对未知的现实无数次尝试靠近的过程中,人类无力地将自己投射于从未知现实中浮现的史莱姆。
[1] 科恩,J.J(1996),《怪物理论:阅读文化》,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第20页
[2] https://lovecraft.fandom.com/wiki/The_Call_of_Cthulhu
[3] 范劲(2021),能否信任黑箱?——《弗兰肯斯坦》中的阅读共同体理想,《外国文学评论》,第二期:47-70
[4] 克里斯蒂娃,J.(1982),《恐怖的力量——论贱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5] 帕利斯,L.(2018),“詹娜·苏特拉‘共生体’”,Vdrome,https://www.vdrome.org/jenna-sutela/
[6] 韦德利奇, S.(2023),《史莱姆:一部自然史》,Melville House,第8章
[7] 伍达德,B.(2020), “电线上的史莱姆”, e-flux期刊#112,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2/352968/slime-on-a-wire/
[8] 韦德利奇, S.(2023),《史莱姆:一部自然史》,Melville House,第244页
[9] 同上,第233页。
[10] 莫顿,T.(2018),《暗黑生态学:未来共生逻辑》,哥伦比亚大学
[11] 梅森,F.(2020),《粘液:史莱姆、粘着、抚摸、混合》,Punctum Books出版,第23-24页
[12] 莫顿,T.(2016),“什么是暗黑生态学?”,《活着的地球:暗黑生态的田野笔记2014-2016》,声音艺术出版社
[13] 桑德斯,L.(2010),“史莱姆菌生长出像东京铁路系统一样的网络”,WIRED,https://www.wired.com/2010/01/slime-mold-grows-network-just-like-tokyo-rail-system/#:~:text=a%20slime%20mold.-.
[14] 哈特,M. 与 内格里,A.(2009),《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企鹅出版,第94页


